“学猫叫”集中体现了我们和猫这种动物的关系。当我们企图以自身的发声器官或语言文字仿拟猫声的时候,我们已经将猫纳入到我们的文化系统之中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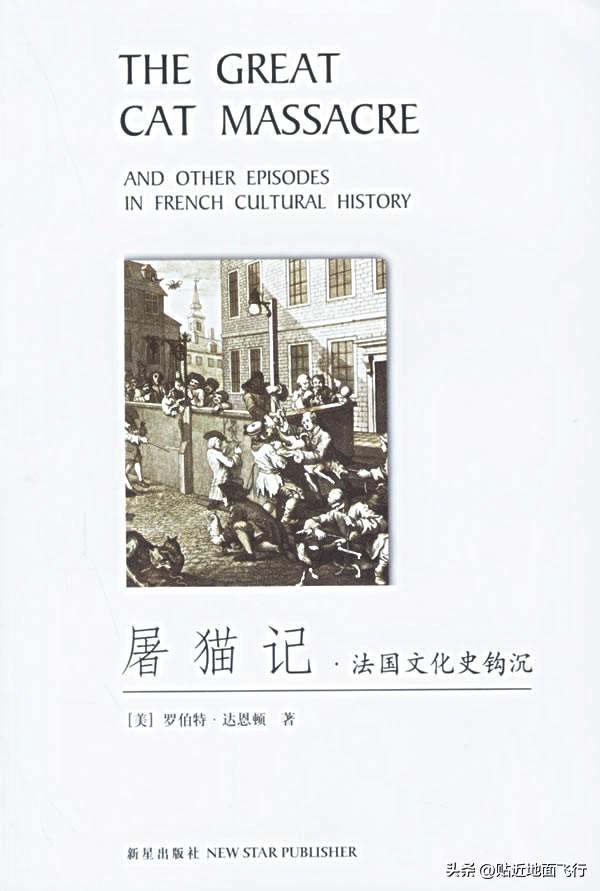
“我们一起学猫叫,一起喵喵喵喵喵”……这支流传大江南北的歌曲,诙谐可爱。近年,它因谐音的缘故,被用来动员民众接种疫苗,又再次传遍大街小巷——一声声“我们一起打疫苗,一起苗苗苗苗苗”,一首老少咸宜的神曲,移花接木般嫁接了重要的宣传信息,毫不费力地便实现了传播的渗透力。
我们的文化有着悠久的“学猫叫”历史。明人龚诩《饥鼠行》一诗有:“狸奴徒尔夸衔蝉,但知饱食终夜眠。痴儿计拙真可笑,布被蒙头学猫叫。”诗歌画面感极强,懒猫、痴儿的形象呼之欲出。这个“痴儿学猫叫”的意象看似自出机杼,实际上却是一处用典。宋人梅尧臣《同谢师厚宿胥氏书斋闻鼠甚患之》有:“唯愁几砚扑,又恐架书啮。痴儿效猫鸣,此计诚已拙。”讲的正是“学猫叫”吓老鼠的“拙计”。古代还有专业的口技表演。清人汪懋麟《百尺梧桐阁全集》载《郭猫儿传》有:“(郭猫儿)尤善象生——象生者、效羽毛飞走之属声音,宛转逼肖——尤工于猫。”这位郭姓口技表演者因为工于模仿猫叫,而以“猫儿”为名,其效果自然也是“宛转逼肖”了。“学猫叫”不仅可用以炫技,而且可用于行鸡鸣狗盗之事。《聊斋志异·保住》中有盗琵琶一节,写了一位身怀绝技的“飞贼”,一人分饰两角,“作猫子叫;既而学鹦鹉鸣,疾呼:‘猫来’”,由此引开看护,调虎离山,从层层高墙中,盗得琵琶。有意思的是,翟理思于1880年在伦敦出版的英译本《聊斋志异》里,“作猫子叫”一处译作:“mewing several times like a cat”,也即是以“mew”转译原文的“叫”这一字眼。“mew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喵”。与“叫”相比,“mew”似乎更胜一筹,将猫叫以文字呈现,学得惟妙惟肖。这也指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。猫叫以什么方式编码于文字之中呢?
“学猫叫”的汉语拟声词
这种情况下,无论采用什么词语,都是要实现摹声的效果。陈望道将语言中引入拟声的修辞方式称作“摹声格”。风雷雨雪、鸟兽虫鱼各有其声,在不同的语言文字中,同一种声音表现方式也大不相同。汉语中,“喵”这个字专用以描摹猫叫,简单的一个音节,鲜活传神。事实上,古人的笔下,并无“喵”叫,而我们习焉不察的语言习惯常反映了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的变化。
古人对猫的叫声有着细致的观察。《本草纲目·猫·释名》中有:“家狸。猫,苗、茅二音,其名自呼。”也即是说猫这种动物因其叫声近似“苗、茅”,故唤作猫。这种“其名自呼”的命名法并不鲜见,尤其在禽鸟方面。鸟名若与其鸣啼之声是对应的,如“布谷”,便认为是自呼其名。梅尧臣《和欧阳永叔〈啼鸟〉》诗有:“满壑呼啸谁识名,但依音响得其字。”猫之所以叫作猫,源自它的叫声。在另外一种文化中,命名并不相同——如英文中,以“cat”命名猫。汉语“猫”与英语“cat”在各自的语言系统里指称这种捕鼠、毛茸茸的动物,源自各自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习惯,在这个意义上,它们与所指称的名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。这也是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。
虽然古人熟稔猫的叫声,并以其声命其名,但在具体的以文拟声的操作上(这里谈的是语言如何摹写猫真实的叫声),他们似乎做了长期的尝试。梅尧臣是禽言诗的集大成者,善于将鸟鸣拟声赋意,表述农事。诗中却未提供“猫叫”的摹写。直至有清一代,读书人也不确定如何摹状猫叫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,嗜食猫肉而命丧黄泉的妇人,死时做“呦呦呦”的“猫声”。《子不语》中,为虎作伥的“伥鬼”幻化为猫等各种动物,叫声却是“汪汪汪”——汪星人和喵星人的界限在这里并非町畦分明。《聊斋志异》一则谈口技艺人学猫叫,写作:“小儿哑哑,猫儿唔唔。”在蒲松林笔下,猫还可以“鸣”。《狐梦》一则中,“猫叫”被用来作酒令。“以狸奴为令,执箸交传,鸣处则饮。”小姑娘为了捉弄客人,“故捉令鸣”,传到他便掐猫,让他连举数觥,一场豪饮。击鼓传觞的风雅变成了“掐猫戏人”的嬉笑。如果不考虑猫的感受,“以手弄猫,猫戛然鸣”成了《聊斋志异》里最具喜剧色彩、略为轻松的时刻之一。故事没有揭露与批判,没有高妙深刻的寓意,却也曲折离奇。
在以文字描摹猫声的道路上,中国文士做了不少有趣的语言实验。在当代的哲学家看来,以文字捕捉纯粹的声音,本身即是语言的要义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不断拓展语言的边界与指称的能力。不过,至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,如何摹写猫语,好像并无定论。在鲁迅那里,猫是“大嚷而特嚷”的动物,让人不得安生;猫打架则是“嗥的一声”(鲁迅《兔和猫》)——鲁迅素不喜猫,有《兔和猫》等针对猫的战斗檄文。刘半农译法国作家左拉《猫的天堂》,写道猫“狠狠地大叫”“口中呜呜然”(左拉《猫的天堂》)。“学猫叫”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。向来对鸟兽虫鱼、博物之学造诣颇深的周作人后来写道:“猫类是很阴的,都很沉默。”(周作人《大虫及其他》)大有盖棺定论之意。在众多的诗文中,“喵”这个字并未出场,以“喵”摹状猫声只是较为晚近的发明。(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“思想工坊”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)
转载请注明:喵喵喵喵喵喵是什么歌,喵喵喵喵喵喵是什么歌曲 | TIKTOK导航 TK123导航 | TikTok运营网址资源导航 TikTok Shop TK小店资源导航 【TK要要要】